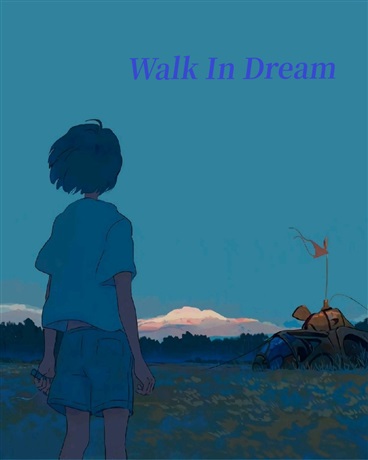“开门。”
黎婉儿自始至终都是高姿态的,就算是现在,也是一幅命令的口吻。
唐菀低低的呀了一声,赶紧从沈执野身上站起来,“我忘了,黎姨说晚上找我有事儿的,野哥,你快去阳台站着。”
洗手间外边就是个小阳台,不是全玻璃的,人站在上面也不怕从外面看到。
唐菀顺势就把沈执野拉起来塞进了阳台里。
沈执野右手手指夹着烟,还不忘摸了摸唐菀的耳垂打趣,“就这么怕她?”
唐菀敛眸,“她是你妈。”
这点沈执野没质疑,把烟含在了嘴里,“出去把我的手表捡一下,在你床头。”
“好。”幸亏他提醒了,不然指定会坏事儿。
唐菀又问他,“还有什么需要捡起来的吗?”一边问又一边用视线在他身上上下打量,他的外套吃饭前她就挂进衣橱里了,避免沾染到饭菜的油烟味。
“别看了,没了。”
男人盯着眼前小女人进展的模样,喉结滚动半晌后,推了她一把,“出去吧。”他知道他妈的脾气的,很急躁。
“好,你要在这里乖乖的喔,不要弄出响动。”唐菀关上门的时候还做了个嘘的动作。
沈执野盯着,一时间有些羡慕她放在自己唇瓣上的那根手指,一时间,也很想去触碰那一份柔软。
这样的念头冷不丁的出现,又冷不丁的消散。
沈执野自己都被其中的荒诞弄得吓了一跳,喉咙像是套上了一个环,一口香烟不上不下被卡在了喉咙上,辛辣的感觉却顺畅的呛进了肺里。
他下意识的收紧腹部要咳嗽一声,却想到了屋里的那个小女人。
被发现,沈执野是不怕的,他也没什么好失去了,名声地位这些,本就不是他在乎的。
唐菀不一样。
她的千怕万怕,她的千叮万嘱。
想到她,沈执野又猛地抽了一口手中的烟,以毒攻毒,用穿喉的辣意压下瘙痒。
烟被抽得猛了,烟头亮起的火星子跳跃不断。
十分急躁。
*
唐菀回到房间收了手表,又四下扫了一圈儿后没有任何异常,才去开门。
沈执野觉得她怕,就大错特错了。
她不是怕,她只是清楚明白,现在还不是两人关系捅破的那一天。
不过,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了。
唐菀想着,唇角抿直,心头涌上的情绪说不明白是兴奋还是烦闷,总之,很复杂。
她甩开心头复杂的情绪,去开门。
黎婉儿已经不是晚宴上的那身装扮了。
她们这种阔太太讲究得很,饭前一身华服,吃饭的时候得换一身不一样的,饭后要是有休闲娱乐,还得再换一身。
她现在穿着一身浅黄色的丝绸旗袍,依旧很隆重华丽,肩头披着淡紫色的披肩,唐菀开门后她没停留皱着眉头就进屋了。
黎婉儿进屋后,没坐,也没问唐菀怎么这么久才开门,而是直接切入主题开了口,“唐菀,我给你找了个工作。”
她的语气强硬,意思很明显了,这份工作,唐菀去也得去,不去也得去。
唐菀问,“什么工作?”
“去韩家做私人保姆。”
私人保姆,是委婉的说法了,说难听点,黎婉儿要她去给人当玩物。
唐菀皮笑肉不笑的扯了扯唇,“哪个韩家呀?”
“最高院前任院长韩友仁。”
黎婉儿说到这儿,脸上终于多了些循循善诱的情绪,补充了一句,“你别怕,他不是坏人,只是年纪大了需要个贴身保姆24小时伺候着而已。”
她这解释颇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。
唐菀知道她就是故意的,黎婉儿也不傻,她就是故意告诉唐菀那韩友仁其实不是什么好东西,然后欣赏唐菀无法反抗只能带着恐惧被自己推下深渊的痛苦神情。
唐菀没如她的愿,不怕反笑,“这样吗?那沈家能从这件事儿上得到多少好处呀?”她问得轻快,话头结结实实的把黎婉儿堵了一下。
黎婉儿瞬间面露不喜,“你什么意思,是觉得沈家需要卖女儿求财?”
“不然呢?难道黎姨转行做中介了?专门给人介绍私人保姆那种?”简称拉皮条的。
唐菀说得云淡风轻,黎婉儿面色倏地变厉,“唐菀,你太嚣张了。”她知道唐菀不是个简单角色,可这样言辞尖锐的跟自己说话,还是头一次。
她有些惊讶,更多的是愤怒。
唐菀依旧淡淡,“黎姨,谈事情平心静气一点不好吗?动不动就上升到讨论情绪上面,这事情还能不能谈了?”
黎婉儿差点没被气个倒仰,却又很快平静了下来,盯着唐菀,“你想怎么谈?”
“我去做私人保姆,韩家给沈家什么好处?”
“这个你知道了做什么?”黎婉儿秀眉挑起,“难道你还想以沈家人的身份分点东西走?”
说完,她正色了起来,“唐菀,沈家千不好万不好,把你养大成人了吧?你吃沈家的米长大,不会长成白眼狼了吧?你就算不念沈家的好,你哥哥对你不好吗?这些年他有多护着你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,现在该你报答的时候了。”
“实话告诉你吧,你去韩家一个月,韩友仁就会联合最高院退下来的那些法官一起投票,将你哥提上一把手的位置。”或许以阿野的能力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提携,但是韩家已经盯上了沈家了,韩友仁最开始看中的是沈明媚,明里暗里暗示过好多次了。
她哪里会把自己女儿送到那种恶心的老变态身边去,光是想想就恶心得三天吃不下饭。
所以她决心换唐菀去。
韩友仁看到唐菀的照片就忍不住了,命令她一周之内赶紧将人送过去,不然,他不仅不会帮忙,还会在沈执野晋升这事儿上压他一下。
原来是这样。
唐菀喉结里滚出了两道笑声,心道,幸亏她是没吃沈家的米吃太多,不然长不长得大都是未知数。
“黎姨,你想要我办事儿,最不应该的就是用所谓的沈家给我的恩情来压我。野哥对我再好,我也只记得他是杀母仇人的儿子。”
她这句话不咸不淡,却掷地有声。
屋里的人都能听到,当然,也包括后面小阳台上的男人。